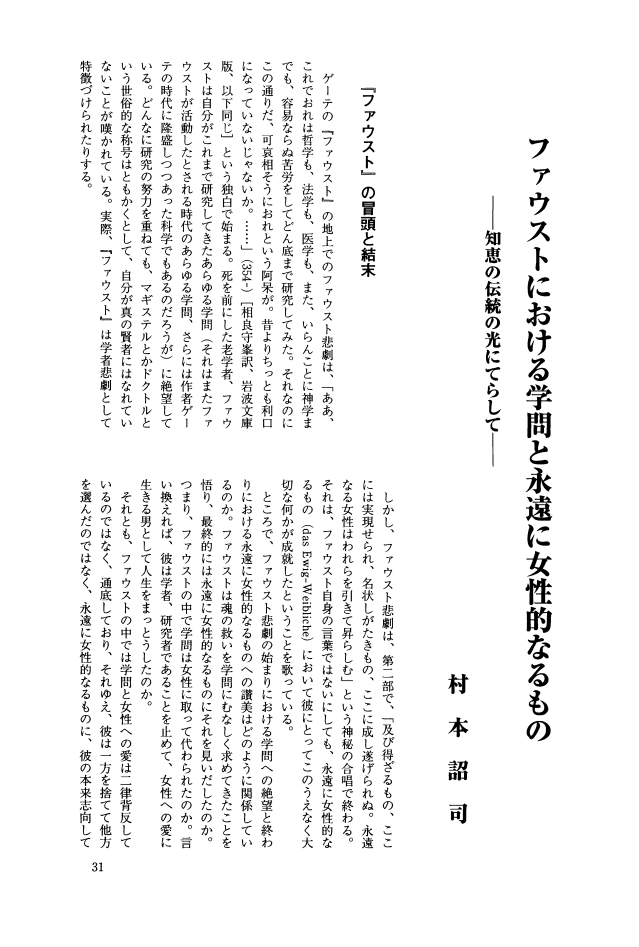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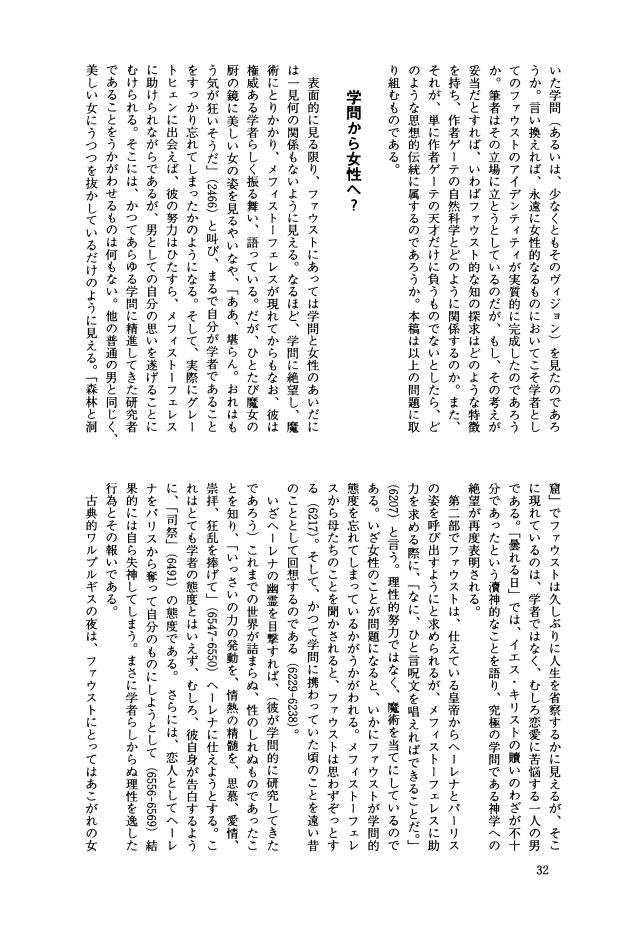
英语原文共 20 页,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浮士德》中的学问与永恒的女性
—在智慧的传统之光照耀下—
村本詔司
《浮士德》的开头与结尾
歌德的《浮士德》中发生在人间的浮士德悲剧,是以“哎,我劳神费力把哲学、法学和医学,天哪,还有神学都研究透了,现在我,这个蠢货!尽管满腹经纶,也不比从前聪明······” (354- ) [相良守峰译、岩波文库版,下同]这段独白开始的。临终的老学者,浮士德对自己穷其一生研究所的学问(也可以说是作为浮士德所活动舞台的那个时代的全部学问,也即作者歌德所处的时代中正日兴昌隆科学)感到绝望。无论再怎样的努力研究,哪怕获得了学士博士这样的俗世荣耀,自己也无法成为真正的贤者,浮士德为这样的自己深深叹息。实际上,《浮士德》正是学者悲剧的典型代表。
然而,浮士德的悲剧,在第二部中,以一段“事凡不充分,至此始发生。事凡无可名,至此始果行。永恒的女性,引我们飞升。”的神秘的合唱结束。这不是浮士德亲口所唱,而是借着永恒的女性(das Ewig-Weibliche)之口对他所达成的于他而言莫大成就的赞颂。
如此说来,《浮士德》开篇时对知识的绝望和结尾处对永恒女性的赞美究竟有怎样的关系?这是否意味着浮士德参悟了学问对拯救灵魂于事无补,最终在永恒的女性那里获得洞见。即《浮士德》中学问的地位为女性所取代。换言之,浮士德的形象从学者、研究者蜕变成了为爱女性而活的男人了。
虽说如此,《浮士德》中的学问与对女性的爱并未陷入二律背反的两难境地,通览全文,你会发现,这是由于浮士德始并不需要面对舍弃一方选择另一方即二选一的尴尬处境,永恒的女性,在一开始就出现在他所贯通的学问(或者,至少在预想中的学问)中。换言之,正是借由永恒的女性这个概念,才使得浮士德这一个性形象得以丰满。以上即是笔者的立场,若是这种考虑得当的话,本文将对浮士德式知识探索的特征,和它与作者歌德的自然科学研究的关系,以及与讨论歌德的天才同样重要的,这种思想所属的文化传统等问题,展开讨论。
从学问到女性?
仅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在浮士德身上根本看不到一丝丝学问和女性之间的交集。原本,对学问感到绝望,染指魔术,直至米菲斯特托勒斯现身,他的言谈举止都保持着权威学者风度。然而,当在魔女的丹房中的镜子里看到美女姿态的那一刹那,他却发出了“天哪,我快发疯了” (2466 )的叫声,仿佛完全将自己的学者身份抛诸脑后。于是,当他真正见到格雷琴时,他便全神贯注地,甚至不惜借助米菲斯特托勒斯的帮助地,去实现作为一个男性的本能欲望。在这里,之前那个醉心于穷究一切学问的研究者形象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似乎是一个和其他男人无异的,对美艳的女性穷追不舍的庸人而已。在“森林与洞窟”一节中,浮士德难得久违地对人生有所省查,然而却并非作为一个学者,而是以一个为恋爱所苦恼的痴情男子的面目出现。“阴天”一节中,借由对耶稣基督殉难方式的批判,宛如神的视角一般,更是再度证明了浮士德对究极的学问,神学的失望。
第二部中浮士德因受所侍奉的皇帝之命召唤海伦和帕里斯的幻影,而向米菲斯特托勒斯求助之际,叫嚷着“什么嘛,不过就是一句咒语的事,你就能把她变出来”。(6207 )并非借由理性的努力,而是依赖魔法的助力,这里似乎暗示着一旦涉及女性的问题,浮士德就会将严谨的治学态度抛诸脑后。然而当从米菲斯特托勒斯那里听闻“母亲们”的事后,浮士德却猛然心惊,(6217 )想起了往昔穷究学问知识的往事。(6229-6238 )
一旦目睹了海伦的幽灵,(他也曾从学问的角度研究过的)他便认识到了时至今日世界的无聊,知晓了本未知道的性事,“将全副激扬的精力,精粹的热情,和癖好,爱慕,崇拜,痴狂献上” (6547-6550 )成为海伦狂热的追求者。这无论怎么说,都算不上学者的态度,不如说,这是如他自己所言的那样,是一种“祭司”的态度。更有甚,想要将海伦作为恋人从帕里斯身边夺走结果导致自己失神晕倒。这简直可称得上毫无学者风范的背离理性的行为。
在古典的瓦普几斯之夜,浮士德的唯一目的便是探寻他所仰慕的女性海伦。除此之外更无其他。当第三幕正式邂逅海伦时,浮士德立下了将她奉为主君来仰慕,向她奉上一切的誓言。(9270-2 )立下了一身兼任共同的执政者,海伦的崇拜者,仆人和卫兵数职的规定。(9362-4 )随之,场景向香艳处切换。
然而,海伦却随着她与浮士德的孩子欧福利翁一起消失了踪影。接下来的第四幕主要是讲述浮士德对自然哲学的考察。(10095-10104,10122-3,10212- 10221)浮士德将米菲斯特托勒斯所寄希望的“欺骗,魔术的幻象,空虚的希冀”一一看破,(103 OO)却难逃终劫。当象征忧愁的女性最终现身,他已经双眼成盲了。这意味着他包含着学问在内人间的全部事业都不可能进行下去了。
与文艺复兴时期愚昧传统的联系
以上所述,都是沿着《浮士德》中学问和女性处于二律背反的对立面这一线索拾级而上,戏剧性的铺陈展开。这种条件下所说的学问,实际上指的是他在开头时已经表示对其绝望的学问,即哲学・法学・医学・神学等学科学问的具体研究,而非普遍意义上的学问。然而,若是浮士德有志于贯通的抽象的学问真正存在的话,那必然不是与女性处于二律背反状态的学问,恰相反,应是一种与女性有着斩不断的深刻联系的学问。
当歌德让浮士德道出对世间一切知识感到绝望的独白时,他或许想到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魔术师阿格里帕.冯.内特斯海姆(Agrippa von Nettesheim,1486-1535 )。阿格里帕在魔女狩猎盛行的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被烙上黑魔术师的烙印,自启蒙主义时代以后又被认为是一个欺诈师。根据传说,他所饲养的黑犬在他死后也紧随之跳入河中自沉而死,自此之后,这条黑犬便以阿格里帕的家奴灵的形象被世人认知。这条黑犬,正是歌德的《浮士德》中在米菲斯特托勒斯暴露真身时出现的黑犬。
然而,历史上真正的阿格里帕却是一位游历了欧洲诸国,与各地的智者交流,精研各种学问,获得了当时条件下能获得全部知识的博学的人。他初期的作品《学问的不定与不实》正是浮士德那段独白的现实来源(De incertitudine et vanitate scientiarum)。实际上,歌德的自传《诗与真》中记载着他宫廷中的友人,时任宫廷顾问的老者劝他读这本书的话语。(HA 9,161-2 )由此,歌德曾受这本书的影响一事,是可以确定的。阿格里帕的这本《学问的不定与不实》沿着尼古拉斯·库萨迪(Nicalaus Cusanus,1401-1464 )的《学识即无识》(De docta ingnorantia )的传统,宣称我们都是无知之人,批判我们所发展的包括魔术在内的所有知识既没有合理的根据,在伦理上也站不住脚跟。
阿格里帕在这本书中引用了罗马时代的诗人阿普列尤斯的寓言故事《金驴记》的一个章节,他所关心的事物,是通常被称为笨蛋代名词驴子。这里的驴子不是单纯的笨蛋的代名词,而是对现存的知识提出大胆的质疑,而使人们接近真理的神圣的无知者的形象。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的故事和这则故事多少也有些相通之处。イエスがロバに乗ってイェルサレム入りをしたのもこれと無関係ではなかろう。虽然宗教传说各自有异,但佛教的《临济录》(柳田1978、202页)中也流传着相似的故事,普化向着临济学驴叫正是这种表现。阿格里帕将它刻画成了超越人知的真理的源泉。然而,从《金驴记》中使主人公从驴子变回人形的是埃及的女神这一点考虑,虽然启示真理的是基督教义中的神明,(或者说,必须是这种神明),其中的女性要素也是不可否认的。他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实际上阿格里帕的老师,正是特利腾海姆大修道院的院长,约翰尼斯·特里特米乌斯(Johannes Trithemius,1462-1516 )。这个特里特米乌斯之后还会提到,正是她的努力,才使得被几个世纪的烦琐哲学所淹没的,那位一二世纪的多才的女子修道院长圣希尔德加德·冯·宾根(Hildegard von Bingen,1098-1179 ),重回文艺复兴时期大众的视野。并以为她写的赞歌(Newman 1987,p.260 )名世。其中不仅盛赞了她那非同一般的圣人般的人品,还有她那博古通今的学问。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30396],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